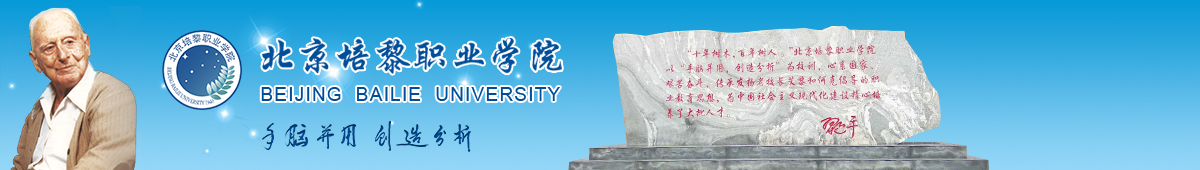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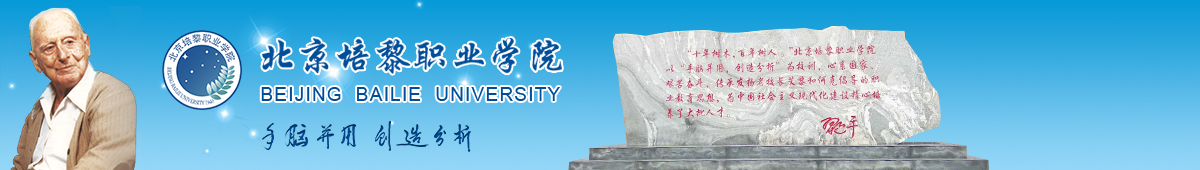

图一
2011年3月2日晚,著名医学科学家吴阶平在北京逝世。
3月3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在吴阶平经常休息和讲课的小房间里,医务人员利用手术和门诊的间隙,前来向这位故去的老院士献花致敬。一切都很平静,仿佛这位94岁高龄的老人并没有离他们远去。
在社区网站上,首都医科大学的同学们用自发的方式悼念这位老校长,一位同学写道:“伟大的泌外之王、首医名人堂的核心、老校长……天堂给您发会诊单了吗?”
在吴老去世后的第三天,我见到了已是国内泌尿外科领军人物的吴阶平的三个“嫡传”弟子。81岁的郭应禄院士,上周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稍稍休息后就赶到了泌尿外科去吊唁;吴老的关门弟子蔡松良教授,风尘仆仆从杭州赶来,只为见到老师最后一面;还有同样刚做完手术不久的鹿尔驯教授也亲自赶到北一院接受采访。
吴老一生有太多的头衔和光环:被奉为“医学界第一人”,主持参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位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会诊,甚至被派往印尼、菲律宾等国家为其国家元首治疗。除此之外他还荣膺多个“第一”:创立第一个泌尿外科、做第一例肾移植手术、第一个确立“肾上腺髓质增生”疾病……无论加在他名字前的称谓是“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都依旧惦记着中国医学的前途,始终没有忘记为他笃信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梦有阶梯
小到一个学科,大到一个国家,都有十年或百年之梦。
中国泌尿外科的第一个梦想诞生在泌尿外科研究所。郭应禄院士告诉我,他很清楚地记得,1998年,吴老和他一起畅谈这个构想:到2020年,中国的泌尿外科要达到国际水平。“老师一直说,赶超赶超,超更重要,我们不能老赶在别人后面。”
在西什库大街的东侧,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每日都在繁忙中接诊来自全国的病人。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1949年,就是在这里,三张简单的病床成为我国泌尿外科的起点;在吴阶平的推动下,1959年又是在这里,成立了设有36张病床的泌尿外科病房;1978年还是在这里,吴阶平创立了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至今它已发展成为集医、教、研、防于一体的泌尿外科中心。历经几代变迁,北大医院老楼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了,但我国泌尿外科的临床治疗和研究却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吴老在中国泌尿外科甚至整个医学界都是“舵手”的地位。“老师非常有远见。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就看到了中国医学发展的趋势,于是成立了结石组,专门负责研究结石。”我国在解放前的结石病患者多为幼儿,而吴老看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引发了不可控制的结石病,就告诉学生“不要等中国结石病多了才开始搞研究,要提前有所准备”。
结石病研究后来归入泌尿外科研究所,但资金始终是困扰吴阶平等人的最大的问题。
“我从美国泌尿外科年会上看到了德国的一种产品叫‘碎石机’,不用开刀就能治疗结石,回来就跟院里说了这个事。但那个时候成立的机构,空有个名字,人和钱都没有。”焦急中的郭应禄等人闻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有对中国的支援,于是就请医院给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打了报告。
“院长回来说,没要着钱。但是对外经委对泌尿外科很感兴趣。”郭应禄等人对此喜出望外,马上找到了已在北京第二医学院(后来的首都医科大学)当校长的吴阶平。详细了解了情况,吴老当即决定马上和对外经委相关负责人见面。
“老师听了这件事后很高兴的,因为但凡对泌尿外科发展有利的他都很支持。所以见到负责人后,两人深谈了很久,最终对外经委同意给我们拨18万美元科研经费。”郭应禄说,他很感慨当时已不在研究所工作的吴老依然对研究所这么支持。“吴老说:‘研究所成立了,不属于我们个人,它是北医的,是全中国的。’所以吴老对研究所的工作一直很关心。”
18万美元对于刚刚起步的研究所来说意义重大。研究所用这些美元购进了国外的先进仪器,之后进行自我研究和改造。在吴老的支持下,与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等国内机构共同研制出我国独有的复式脉冲碎石机,为国内医疗水平的提升提供了硬件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所利用这18万美元中的一部分,送郭应禄和顾方六等8个人分批到美国、瑞典等国家学习,解决了研究骨干的问题。郭应禄告诉我,当年出国学习的这8个人,在国内泌尿外科界都是领军人物。
但一个研究所对于整个中国泌尿外科而言,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在吴老看来,泌尿外科研究应该敞开大门,吸纳更多的人才加入研究队伍。“吴老的那本《吴阶平泌尿外科学》是在烟台定稿的。当时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怎么看中国泌尿外科的现状。”郭应禄院士说,当时的中国由于“文革”后出现了人才断层,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人才外流,所以泌尿外科急缺业务和研究骨干。
中国泌尿外科的路到底该怎么走?深沉的思考萦绕在吴阶平的心中。
“咱们能做点什么?”吴阶平向学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最后我们认为,培训应该面向全国。”1994年在颁发“吴阶平、杨森奖”期间,组委会决定成立一个培训中心,培训年轻医生。不久吴阶平等人又筹备了培养学科领军人物的“将才工程”,全国各地的泌尿外科博导和硕导都来接受培训。今日的北京大学泌尿外科医师培训学院,已为全国培养和输送了数以万计的高水平的泌尿外科医生。尤其让吴老欣慰的是,美国泌尿外科年会在2006年年会的前一天,为中国免费提供了一次华语会场。这标志着中国泌尿外科研究水平终于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但我们应该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达到,只是说最高水平达到。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地方连基本的医疗保障都没有呢!”自豪后的郭应禄院士如此回应道。而在此之前的2004年,中国泌尿外科又提出了一个百年的梦想:100年后,中国泌尿外科水准世界领先。
郭老告诉我说:“这是我们中国医学界的梦想,更是吴老一生的梦想。”
公心为大
在北大附二医院的一间教室里,一百余人坐在讲台下,看着吴阶平举起紧握的拳头,向党旗宣誓“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时间是1956年1月27日。当时的北大附二医院还在府右街北口,为吴阶平入党,支部专门召开了一次公开会议。台下的一百多人都是慕名而来,也算是接受一次教育,其中包括郭应禄。

图二、吴阶平(左)和郭应禄
这是吴老留给郭应禄的第一印象。“当时吴老在支部会上说,自己学了知识就是要报效祖国的。”三位老前辈说吴老给他们影响最深的,是作为一名党员的大公无私。
“公”,指的是国家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吴阶平毕业于医学界的金牌学校——美国人办的协和医学院。然而他在协和学习的时代背景,却是日本入侵中国造成的炮火连天。吴阶平师从我国最早的泌尿外科专家谢元甫教授。1947年,谢教授设法把刚刚工作五年的吴阶平送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
吴阶平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是赫金斯教授,后者是现代肿瘤内分泌治疗的奠基人之一,并曾获诺贝尔奖。这个年轻有为的中国人很得赫金斯教授赏识,业务能力突飞猛进。毕业时,赫金斯教授千方百计要把吴阶平留在美国,许给他很多特殊待遇。当时芝加哥大学正在为赫金斯建科研楼,他甚至把一张蓝图摆在吴阶平面前,诚挚地指点着说:“这里是你的实验室,你可以把家人接来……”
而在大洋彼岸,那个伤痕累累的国家甚至连基本待遇都不能保障。鹿尔驯老人告诉我,当时的北大医院,有的仅仅是狭窄的走廊和早已过期的仪器设备。
像很多老一辈科学家一样,面对国外的高薪待遇,吴阶平不为所动,连行李都没带,急匆匆赶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回到了祖国。生在和平之日的大多数人也许不能理解,在上个世纪中期那些顶着“博士”头衔的人,为什么会为“报效祖国”这个词热血沸腾。而故去的吴老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懂得了“公”字背后的分量,虽然彼时的他还不是共产党员。
但其实吴阶平和共产党员很早就有接触。
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吴阶平在一篇文章中说,他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并且“的确是受了一次比较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之后,有些人放弃了原来的学业转而去了延安。吴阶平写道:“有人来找过我,是长期在北京做地下工作的。他看我很爱国,也经过‘一二九’运动,他说你要不要去延安?我说我愿意去。他说那我跟(给)你联系联系。”
延安是革命圣地,是多少人做梦都想去的地方。然而吴阶平确实没有去成延安。抗日战争开始后,吴阶平到了中和医院(后改名为“人民医院”),院长叫钟惠澜,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当时北平的环境很危险,很多地下工作者不敢去医院看病。那位地下工作者又找到了吴阶平,请他出诊。“我说可以呀,他就给我写些地名,我就骑着自行车各处看病。”在看病的过程中,吴阶平也接受了一些革命道理,并对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但即使是他自己恐怕都不知道,为共产党员看病,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德行天下
“正其时而逢周公恩来,承教诲而幸遇知音。共国事和医政,恰珠联与璧合。”这是2002年吴阶平从医60周年时,高士其基金会秘书长高志其撰写的《大医赋》中的一句话,道出了周恩来和吴阶平的交情之深。
1976年1月7日,一代伟人周恩来留下了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

图三、吴阶平的三个“嫡传”弟子:蔡松良、郭应禄、鹿尔驯(左起)
周恩来临终的留言在吴阶平的心底铭刻了一生。至今在吴老家中的书柜上,还有一张周恩来总理的黑白照片。三位老先生说,总理的言传身教给了吴老“终身难忘的教诲”。
需要吴阶平的人确实很多。
“文革”前吴老的学生中顾方六先生已经去世,现在只剩下郭应禄院士。时间过去很久了,图书馆的书架上落了一层又一层的灰尘。翻开1965年的《中华外科杂志》,《精囊肿瘤》一文下作者的署名只有“郭应禄”一人。提到此事,郭老十分感慨。“当时是一个武汉的病人,从武汉到上海都没治好,就到了北京,最终找到了北大医院。吴老给他做了检查,查出了精囊癌,于是赶快给他做了手术,我也上(手术)台了。”术后郭应禄做了手术总结,并写了一篇论文,请吴老指导。吴老做了指导后,拿着论文找到了另一个导师沈绍基。吴老问沈绍基:“郭应禄写了一篇文章,第一次发表。我的名字就不要了,你的呢?”沈绍基也很痛快地回道:“我也不要啦!”郭应禄感慨地说:“我当时就是参加者,后来整理了材料而已,没想到吴老态度很坚决,不要署他的名字,所以最后只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除了对郭应禄等亲手带出来的学生,吴老对所有泌尿外科医生的进步都很关注。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名誉主席的吴阶平到常州主持常州二院的泌尿外科项目鉴定会。鉴定会间隙,泌尿外科主任医师陆曙炎向吴阶平提出,很想到国外去看看,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引荐。“没想到吴阶平一口答应了下来,更没想到的是,他一直在心上记了好多年。”
在1995年国际泌尿外科进展研讨会召开期间,陆曙炎再次见到了吴阶平。“我和他都在会场休息,他请秘书来找我去见他。原来,他在会上特别向当时国际泌尿外科学会的主席霍恩福勒介绍了我的情况,引荐我到德国进修,对方也答应了。”吴阶平还告诉陆曙炎,德国也是用英语交流,相关的技术很好,且开放程度高,有机会参加手术。陆曙炎说:“这件事让我很感动。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他还能记住。”
接触吴老的人都说,吴老在临床上向来以严谨著称。郭应禄做吴老研究生的第一年,吴老经常带着学生们查房。“那个时候我们要把病人的详细情况都背下来,所以老师查房之前,我们都很紧张。”恰好有一次,查到了郭应禄的一位患了肾结核的病人。吴老检查时摸了一下患者的下身,然后问郭应禄:“你检查了他身体有什么发现吗?”郭应禄答道:“没有。”吴老说:“你摸一下下身。”郭应禄摸到患者下身发现附睾上有肿瘤,“我当时脸一下就红了。可是老师没有当着病人的面批评我,只是出了病房后跟我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心虚的郭应禄站在办公室里,按他的话说“摇摇晃晃”。吴老见状招呼他坐下。“吴老跟我说,病人把生命交给咱们,咱们就要一丝不苟地对他负责任。我相信你的水平是能够查出来的。”简短的交谈中没有指责,却让如今年过八旬的郭应禄记忆犹新。
“吴老很早就认识到中国泌尿外科起步晚,需要不断完善,因此他具有虚怀若谷的学者气度。”蔡松良忆起吴老时说道。《吴阶平泌尿外科学》到现在已经修订和再版过很多次,成为很多泌尿外科医生的必读书。正是这本书,让他成为了吴老的关门弟子。
1983年吴老在浙江医科大学办讲座,很多人来听课。站在讲台边上的,就是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蔡松良。“因为他的那本《吴阶平泌尿外科学》我已经翻过很多遍了,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他,但是不知道他这个人的气量怎样,所以心里很忐忑。”讲座结束后,蔡松良恭敬地上前问候吴老:“您刚刚的讲座说了很多,我感触也很多,但是泌尿外科那本书里还是有些问题想和您探讨一下。”
“吴老马上就说:‘岂止是问题啊,还有很多错误呢!’他的气度让我很佩服。于是就为了他这句话,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了39页纸的意见寄给他。”蔡松良说起吴老时很激动,眼睛微微泛红。不久之后,这个写了39页意见的人看到了《光明日报》上吴老的招生启事,便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即将晋升为副院长的机会,转而到北京求学,成了吴老的关门弟子。
“名相已逝而名医犹存,然圣贤精神存乎人心,弥于天地,此诚国之幸也。”《大医赋》里的这句话,道出了吴老对中国泌尿外科发展毕生的挂念和关照。“立足北医,放眼全国”这是吴老带领学生们倾注了一生心血的事业。名相名医皆已逝,但2011年的这个春天,我们并不感觉到寒冷,因为“圣贤精神”依然存于人心。等待中国医学人的还有未完成的百年之梦,等待中国共产党人的也还有未完成的复兴之路。